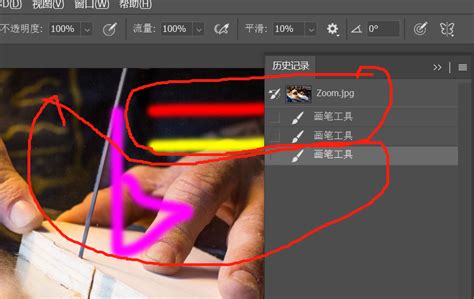‘壹’ 莫迪里阿尼的肖像作品戴帽的弗劳将所画人物的脸型和脖子都拉长并简化为什么
是莫迪里阿尼自己内心的镜像,是孤独的象征。
对于漂泊巴黎整整14年的意大利人莫迪里阿尼,孤独感是肯定存在的,漂泊无根,无所可依的那一份浓郁的乡愁,是弥散在他画里画外的。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他对形式的探索和创新。这些女人的肖像,再没有他早期丢勒的写实风格;这些女人的裸体,也不是古典主义的希腊之美,
不是克里姆特雍容华贵的华丽之美,不是雷诺阿的光与色夸张的塑造,也不是席勒的那种充满狰狞的情欲的宣泄。他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他们都拉开了距离,让我们可以欣赏到区别于古典、印象、现代主义几大流派所表现的另外一种美。
(1)莫迪利亚尼珍妮的眼睛为什么没有扩展阅读
在20世纪之初各种艺术流派纷繁树立各自大旗的巴黎,莫迪里阿尼以自己特立独行风格的画作,树立了别人无法归属而属于自己的流派。如果看过珍妮和阿赫玛托娃的照片,再来看莫迪里阿尼画的珍妮和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会觉得照片上的珍妮和阿赫玛托娃漂亮。
但再看那些画像,又会觉得画比照片更简洁,更耐看,更富有性格,更让人充满想象。这便是莫迪里阿尼艺术的魅力。他一下子把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那些须眉毕现逼真透顶的人物肖像,拉开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像,像照片一样的像,再不是人物像画作的唯一标准。
‘贰’ 莫迪里阿尼的禅的阐释
但是,这谜一样的人物、谜一样的绘画,还不是他的艺术魅力之全部。当我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来讨论莫迪格利阿尼时,我对他的理解便更进了一步,这个视角就是禅宗。尽管听起来好像荒唐,因为莫迪格利阿尼与禅宗毫无关系,可是,西方古典哲学与禅宗也毫无关系,但却并不妨碍海德格尔用禅宗的眼光和禅宗的方法去研究之,并由此而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总不能只用西方眼光看西方艺术,总得有与众不同的东方眼光才是。如前所述,莫迪格利阿尼的裸体画,没有画外的寓意,他只关注人体本身,于是就有了色情的嫌疑。这让我想起美术史和禅宗的两个公案。1863年,马奈在巴黎沙龙展出《草地上的午餐》,因为画中的裸体没有寓意,既非神话故事也非历史题材,而是现世生活的写照,结果被认为不知羞耻。拿破仑三世看到这幅画,破口大骂、挥鞭相向。奇怪的是,当拿破仑在同一沙龙看到卡巴纳尔(Alexandre Cabanel, 1823—1889)的裸体画《维纳斯的诞生》时,却立刻就抛出银子买了下来。卡巴纳尔的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笔力于美貌女裸体,其脂粉气与布格柔(William Bouguereau, 1825—1905)的宫廷式裸体画如出一辄。但是,卡巴纳尔在天上画了几个飞翔的小天使,将裸体的背景画为大海长空,将人物的肌肤抹得像希腊雕塑那样光滑细嫩,再配上古希腊神话的题名,于是就有了古典主义的寓意,就不是不知羞耻了。在这个美术史的公案中,由于所谓古典的神话寓意,拿破仑盲目了,他对卡巴纳尔的色情诱惑视而不见。莫迪格利阿尼的有目无珠,是一种着意的盲目。禅宗讲究有与无,讲究有中之无、无中生有。海德格尔的“存在”、“此在”与“彼在”,也涉及这个问题。一则禅宗公案说,一休禅师有次率徒淌水过河,见河边有一女子因水急而不敢涉足,便背起那女子,负她到了对岸。此事过后好几个月,一个小徒弟终于忍不住了,问一休,你口口声声让我们远离女色,可是你自己却背女人过河,这是为什么?一休回答说,我只不过背她过河,你却背了她好几个月。当然,这个故事有点刻薄,我不相信一休会这样挖苦自己的弟子,他不会那样小心眼。这个公案,讲的就是有与无。一休把一个人背过了河,并不在乎这人是男是女,他心里没有色,而小弟子却满心是色。莫迪格利阿尼的裸体画,关注的是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激情。观画者若像一休的弟子那样戴上有色眼镜看,那么,这些画当然是色情的。拿破仑是伟人,但也附庸风雅。他戴上寓意的眼镜看画,马奈就是无耻的色情,而卡巴纳尔就是高雅的古典。莫迪格利阿尼的“有”与“无”,全在于他的内心,他并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莫迪格利阿尼因健康不佳,需要女人帮助,长期生活在女人圈中。早年母亲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后来到巴黎,又与众多烟花女过从甚密,并且还有碧萃丝和杨妮的呵护,所以对女人别有一种情愫。他的裸体画,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愫,至于是否色情,只好见仁见智,反正他的画,照传统的学院派标准看,全无寓意可言。一个着名的禅宗故事说,当年禅宗五祖要传衣钵,大家都以为会传大弟子神秀。神秀作偈,强调心如明镜,须要时时拂拭。那时惠能在厨房做饭,作了一首针锋相对的偈陀,拿出去对应师兄。惠能写到,心中本来就没有尘埃,哪里需要拂拭。五祖有慧眼,洞悉惠能偈中真谛,遂以衣钵相传,惠能成六祖,由此开南宗。不可否认,在莫迪格利阿尼的一些画中,确有情色成份,但画家真正在意的,是形式与激情。在莫迪格利阿尼短短的一生中,他只画肖像和人体,这些画,又只画人物不画背景,而人物又往往有目无珠,画家总是向内看。这就像打禅,画家专注于一种题材,心无纤尘,不厌其烦地反复画,画得多了,自会悟道,得以尽享作画之乐。这种专一,有如禅宗所谓“定慧”,唯其如此,莫迪格利阿尼的绘画才可能炉火纯青,也才会如此动人心魄。老子《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莫迪格利阿尼的形式与情色,让我们盲无所见,而他的专一,又让我们看到他对内省的执着。五月在纽约看画展,适逢犹太博物馆的“莫迪格利阿尼不再神秘”开幕(±Modigliani: Beyond the Myth,2004年5月-9月),我有幸第三次看这位画家的作品。第一次看莫迪格利阿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回顾展,是十多年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画家的色彩中流露出的激情和执着,让我难以忘怀,自此对莫氏产生了好感。第二次看莫迪格利阿尼,是去年夏天在洛杉矶美术馆,那里有“莫迪格利阿尼与蒙巴纳斯艺术家作品”大展。蒙巴纳斯(Montparnasse)为巴黎地名,二十世纪初,从欧美各地前往巴黎从艺的年轻穷艺术家,不少都聚居在那里。后来我去巴黎,还专门到蒙巴纳斯寻找莫迪格利阿尼和巴黎画派的遗踪。我对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和巴黎画派一向情有独钟,而莫迪格利阿尼又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我喜欢他用单纯和情绪化的色彩、用即兴的笔触,来画变形拉长了的肖像及人体,喜欢他以此表达对生活的一腔激情。通常,美术史学家们在讨论他的艺术时,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他同过去的画家作比较,认为他的画具有抽象形式和情色内容。作品拍卖2013年,佳士得拍卖行在伦敦举办的一场以印象派和现代艺术为主的专场拍卖会,共拍得1.36亿英镑(约合13.32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佳士得每年2月在伦敦举办的同类型拍卖会的销售纪录。这批作品中售价最高的是一幅由意大利艺术家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于1919年创作的《戴帽子的珍妮·海布特》肖像画,以远超过估价的2690万英镑(约2.64亿元人民币)成交。
声明:易商讯尊重创作版权。本文信息搜集、整理自互联网,若有来源标记错误或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纠正并删除相关讯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