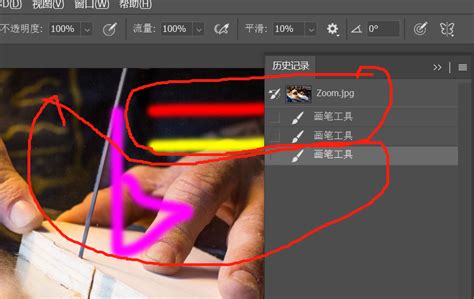1.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心理描写
托尔斯泰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作家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
聂赫留道夫公爵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一次他参加审理两个旅店待役假手一个妓女谋财害命的案件。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道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受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瑕。三年后,聂液游赫留道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路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道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娃被审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名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
聂赫图道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庆: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僧”。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暧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道夫到监狱探望玛公洛娃,向她问起他们的孩子,她开始很惊奇,但又不愿触动创伤,只简单对答几句,把他当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卢布烟酒钱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又去探监并表示要赎罪,甚至要和她结婚。这时卡拿唯秋莎发出了悲愤的指责:“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后来聂赫留道夫帮助她的难友,改善她的处境,她也戒烟戒酒,努力学好。
聂赫留道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道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闹敏销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道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类应该相亲相爱,不可仇视”的启示。
心理描写:
指对处在一定环境中的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它是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能够直接深入人物心灵,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列夫•托尔斯泰是位擅长心理描写的巨匠,他在《复活》中写玛丝洛娃在监狱里以犯人身份会见前来探视她的贵族地主聂赫留道夫,“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往下,就进入往事的回忆。起初,她心头掠过一丝美好的回忆,因为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曾经爱过她并且为她所爱;接着,她想起他的残忍作为,想起他留给她的痛苦和屈辱。这些至今仍象磐石一样压迫着她,使她无法摆脱,她痛恨这个毁了她幸福的人,于是记忆中那种爱情的幻境顿时化为泡影。但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又想利用他一下。这段心理描写既预示着聂赫留道夫后来应允为她请律师的情节,也预示着他希望用对玛丝洛娃的描写还有助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2. 《复活》玛丝洛娃人物形象是怎么样的
《复活》玛丝洛娃人物形象分析如下:作者叙述了玛丝洛娃悲惨的身世与坎坷的经历,并与她善良的本性进行对比,将玛丝洛娃塑造成了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
这些一波三折的剧情与对其善良性格的描写塑造了玛丝洛娃的定位:一个饱受生活迫害,惹人同情的年轻女性。
肖像评述
据说这段描写作者曾反复修改过二十几次。从这幅玛丝洛娃的肖像看,那“仍旧放光”的眼睛,依然保存着夕日玛丝洛娃的纯真;而那苍信唤白的面滑旦凯色,以及故意让它溜出来的“一两咎头发”,便显出她长期受侮辱迫害和堕落过的痕迹。
还有那只非常有生气而带点斜睨的眼睛,则隐含着她对社会的不满和蔑视。这样写,既符合她过去的经历,又表现了她现时的身份;不但使读者如见其人,而且还可通迟慧过她的外表,窥见她的灵魂。
3. 《复活》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及作用
梦想与现实本来是没有距离的,只不过一个在心里,一个在眼前!
在生活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角色,何必要求这个去扮演那个呢?那是不会成功的,也许是自己也扮错
了角色,可是谁又知道自己该演什么不该演什么呢?等你发现自己演错了戏;你的舞台也将人散灯尽!
你把生活设计成一场赌局,得到的却是暂时的快感,你在赌局中投入的感情和精力越多,全盘皆输的可能性就
越大,就可能得到越多的伤害,你不该抱怨,游戏的规则就是如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愿赌服输”。
走过太多路~淋过太多雨~明白冬来雪飘~花开花落的道理~寻的;只是那份家的安定~
你的文凭代表你应有的文化程度,顷掘樱它的价值,会体现在你的底薪上,但有效期只有三个月!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做回忆;想要得到的,必须
努力;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泪水和汗水化学成伤相似,可是前者只能让你获得同情,而后者却能让你获得成功!
童年似流水一样的过去,时光是不老的,散绝老的是人。走在时间里的人,雀丛于纷扰的世间,忙碌着做一些可有可无
的事情。混迹于人群中失去自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模样了。
人生是一张单程车票,失去的便永远不会再拥有。千万别把美好的生命浪费在等待上,把握现在,享受现在,
才是最重要的。
走在一起,是缘份。
一起在走,是幸福!
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
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之后就不要悔恨。
生话的事就象在寒风中吃雪糕一样,在冰冷的后面感觉甜蜜!
有受过冻的人才会知道暖是来之不易。
好好生活吧,祝福你成功!!
4. 《复活》中审问的片段
玛特维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因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方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有时越过眼镜有时透过眼镜看看被点到名的人。
“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相貌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答应。
“旦竖退役上校伊凡诺夫。”
“有,”那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和颜悦色、笑得咧开嘴巴的商人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越过眼镜向他瞧瞧,特别恭敬而愉快地向他鞠躬,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分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指指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互相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块绿呢桌布,边缘饰着深绿色穗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麻栎扶手椅,椅背很高,上面雕有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框里嵌着一个色泽鲜明的将军全身像①。将军的军服上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供陪审员坐的,高台下面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两部分,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法庭后半部的前排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又象工厂的女工,又象公馆里的女佣,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锁住了,因此交谈时怯生生地压低声音。
①指沙皇像。
陪审员们一姿没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
“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走到台上:领头的是体格魁伟、留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在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家里不开饭。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店去吃饭了,”内弟笑着说。
“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向来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遵照医迹迟纳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因此今天他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气,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不同方式预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要是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定能治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但他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慌忙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立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食品店里盛糖果用的玻璃缸和墨水瓶、钢笔、白纸以及几支削尖的粗细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么拼命摆动一只手,迅速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还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向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和阅读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再好好看一遍。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长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位子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仿佛在嘟囔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玛丝洛娃坐下来,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象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上浮肿,脸色白中带黄。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吞吞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去。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象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陪审法院开办以来①他就在区法庭任职,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多达几万人,而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给家人留了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人们起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这一点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仅从来不感到于心有愧,而且还很喜爱它,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只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到手一万卢布。
--------
①俄国在一八六四年实行司法改革,成立陪审法院,刑事案件公开审判。
等陪审员都顺着台阶走到台上,司祭就侧着花白头发的秃头,套上油腻的圣带,然后理理稀疏的头发,向陪审员们转过脸去。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手指并拢,象捏住什么东西。“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顿一顿。“手这样举好,不要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子的相貌堂堂的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很有精神,看上去很高兴,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有点勉强,不大乐意这样做。有些人念誓词念得特别响,仿佛有意在挑衅说:“我照念就是了,照念就是了。”有些人只是喃喃地动动嘴巴,落在司祭后面,后来忽然惊觉了,慌忙赶上去。有些人恶狠狠地使劲捏拢手,仿佛怕落掉什么东西。有些人把手指松开又捏拢。个个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怀信心,自以为在干一件有益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挤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烟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蒂,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大家又回到原位,跨过别人的脚,在两排高背椅上坐好。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耽搁,气氛十分庄严。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使参加者都很满意,更加坚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左臂肘上,一会儿支在右臂肘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弄齐一叠纸,一会儿摩挲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铅笔。
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与外界私通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庭长讲话完毕,就向几个被告转过身去。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颊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地急急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你的身分是什么?”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吃过官司,因为我们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有吃过官司吗?”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出酒气,勉强忍住饱嗝,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吃过。”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庭长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
但西蒙仍旧站着,把包奇科娃挡住。
“卡尔津金,请坐下。”
卡尔津金还是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但卡尔津金一直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侧着头,不自然地睁大眼睛,不胜感慨地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
他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象站起来时一样快地坐下,把身上的长袍裹裹紧,颊上的肌肉又不出声地抖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不胜疲劳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不瞧她,只顾查阅着面前的文件。对于庭长来说,审理案件已是家常便饭,若要加速审讯,他可以把两个案件一次审完。
包奇科娃四十三岁,出身科洛美诺城小市民,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包奇科娃回答问题非常泼辣,那种口气仿佛在回答每句话时都说:“对,我叫叶菲米雅,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我觉得挺有面子,谁也不许嘲笑我。”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坐,就立刻自动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特别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你得站起来,”他发现玛丝洛娃坐着不动,和颜悦色地说。
玛丝洛娃身姿矫捷地站起来,现出唯命是从的神气,挺起高耸的胸部,用她那双笑盈盈而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直盯住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迅速地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审问,挨个儿瞧着被告。他眼睛没有离开这第三个被告的脸,想:“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你登记的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不作声。
“我问你,你的真名字叫什么。”
“你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这不可能,”聂赫留朵夫嘴里仍这样自言自语,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确确实实是热恋过的姑娘,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想她,因为想到这事实在太痛苦了,这事使他原形毕露,表明他这个以正派人自居的人不仅一点也不正派,对那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十分下流。
对,这个女人就是她。这会儿他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的神秘特点。这种特点使每张脸都自成一格,与其他人不同。尽管她的脸苍白和丰满得有点异样,她的特点,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还是表现在脸上,嘴唇上,表现在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烂漫、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在脸上和全身流露出来的唯命是从的神态上。
“你早就该这么说了,”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父名叫什么?”
“我是个私生子,”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照你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你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心里仍在琢磨,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你姓什么,通常人家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通常用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分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你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院里,”她说。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院您自己知道,”玛丝洛娃说。她噗哧一笑,接着迅速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盯住庭长。
她脸上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她的话、她的微笑和她迅速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可怜,弄得庭长不禁垂下了头。庭上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接着,这种寂静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了。有人向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
“你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审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象盛装的贵妇人提起拖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来,一双白净的不大的手拢在囚袍袖子里,眼睛一直盯住庭长。
接着传证人,再把那些用不着的证人带下去,又推定法医,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响很清楚,但因为念得太快,混淆了舌尖音和卷舌音,以致发出来的声音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搁在桌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要打呵欠,都勉强忍住。
几个被告中,卡尔津金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偶尔用一只手指伸到头巾里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忽而一动不动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忽而全身抖动,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沉重地叹着气,双手换一种姿势,往四下里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展开了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声明:易商讯尊重创作版权。本文信息搜集、整理自互联网,若有来源标记错误或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纠正并删除相关讯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