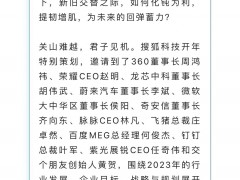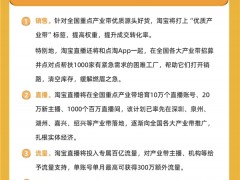2016年,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又一个关键性年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多年相比,经济增长率明显地慢下来,从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一路下降到7%左右,并可能进一步下降到7%以下。同经济增长慢下来相应的是,投资率、进出口增长率等也显著地慢下来。而且,人们明显地感受到,尽管简政放权的改革在推进,但各级政府的办事程序却在慢下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业务节奏也在慢下来,甚至最具创新性特征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业务流程也都走上管理程序越来越繁琐的高度行政化模式。尽管文件下得又多又快,但新常态似乎就是“慢常态”。
如果说“慢下来”是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过程性特征,那么,新常态中要实现的目标却不应是可以“慢慢来”的任务。相反,我们的期望仍然是要争取“快上去”:产业结构调整要“快上去”:从中低端升级为中高端;收入水平要“快上去”: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小康社会要“快上去”:2020年达到全面建成目标;扶贫脱贫要“快上去”:立下“军令状”,确保攻坚战按期决胜;科技创新要“快上去”:尽快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实现创新驱动……总之,“慢下来”的现实,并没有磨灭“快上去”的期望和决心。
“慢下来”是一种客观态势,“快上去”是所选择的奋斗目标。因此,进入经济发展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历史转折期,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既要避免“急于求成”和继续“不惜代价”扩展数量规模,又要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即形成“慢下来”与“快上去”的有效契合,就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度过历史转折期必须回答的“斯芬克斯之谜”。这就像是要求司机不可超速行车,不可违章驾驶,但仍然必须按时达到其他人须用较长时间才能到达的遥远目的地。于是,另辟蹊径的改革与走创新之路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而这一可行路径的基本特征必然是“稳中求进”。“稳”是“慢”的底线,“进”是实现“快上去”目标的必由之路。因此,减速稳行绝非踌躇不前,相互掣肘,贻误战机。
问题的要害是:今天的“慢下来”是对以往的超高速所导致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的报复,因此,实现“慢下来”与“快上去”的契合,不能再依靠超高速时期的那种不可持续的刺激方式和过度松弛的法纪约束,但是,也不可以没有必要的激励机制,更不能让发展的激情熄灭。因此,即使认可了“慢下来”,也仍然需要保护经济主体,包括各级政府的发展热情和创新精神,保护他们敢于“闯”,敢于“试”,敢于改革,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品性。
既然进入新常态,过去的一些老观念、老做法就会过时,不再适用。新常态对于所有的人都是新情况、新挑战,许多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感觉面临“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而“不知道该怎么干”,就可能成为普遍性现象。不过,必须从深化改革中寻求出路,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必须通过加快改革,激发微观活力,突破障碍瓶颈,将“慢下来”中蕴含着的“快上去”因素,孕育为实现“快上去”目标的持续性能量。如同创新孵化器那样,催生新常态中的强劲发展动因,让深藏于中国巨大经济体中的发展能量再次迸发,就可以让“慢下来”成为“快上去”的蓄力期。
必须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的是,中国的改革历经30多年,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历史时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根本性改革时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当前的“慢下来”尽管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具决定性的还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即由于改革不到位而产生的现象,所以,决不能长期停留于“慢下来”尤其是改革“慢下来”的胶着状态中。如果说,短期性的“慢下来”可以是良性的调整,那么,长期性的“快上去”才是历史进步的实质表现;尽管一定时期的“慢下来”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能够彪炳于史的终究还是“快上去”的目标达成。
总之,新常态决非一味“慢下来”的节奏,更不是甘愿认了“慢就慢”的宿命,甚至“宁慢勿错”,人为强化流程中“懈慢”与“繁琐”的循环累积,不明所措,相互推诿,听任失速。2016年,之所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性年份,就是因为,它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改革攻坚之年,稳中求进之年,以“慢”取“快”之年。